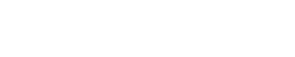2020年6月4日下午,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及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一审判处被告人韩某勤有期徒刑九个月、被告人韩某华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另判决上述两被告人赔偿渔业损失75890元并赔礼道歉。
具有昭示作用的判决
法庭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5日至9月17日,两被告人韩某勤、韩某华及其雇佣人员先后9次选择夜间,在长江上海段长兴水域、长江上海段九龙港附近水域,使用以电脉冲方式辅助捕捞的拖曳三重刺网,采用在两船之间拖拽电鱼网的方式,共捕捞花鲢3700余斤、白鲢140余斤、长江鲈鱼1000余斤。
两被告人第9次售卖渔获物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经认定,9次非法捕捞行为所得渔获物价值共计75890元。经评估,两被告人使用的渔具属于禁用捕捞工具。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遂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向法院移送起诉,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两被告人赔偿渔业资源损失75890元、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此案的案情并不复杂,两被告人的行为主要有四个环节值得注意:一是两被告人共计9次选择夜间进行捕鱼;二是捕鱼的地点是在长江上海段的长兴水域、长江上海段的九龙港附近水域;三是捕鱼使用的是以电脉冲方式辅助捕捞的拖曳三重刺网(俗称“电捕鱼”);四是9次捕捞行为所得渔获物价值共计75890元。
在庭审过程中,两被告人供认,9次捕鱼的地点都是在长江水域,选择在夜间捕鱼是为了避免被人知道,使用在两船之间拖拽电鱼网的方式是为了降低成本、增加收入。法庭经过辩论确认,又经过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对渔具评估,两被告人使用的渔具属于禁用的捕捞工具。也就是说,两被告人明知所采用的捕捞方式是非法的,为了获取利益依然我行我素。
两被告人长期在长江干线从事捕鱼,明知国家渔业环保的相关政策,依旧进行非法捕捞行为,数量较大、涉案金额较多,影响较大。本案作为公益诉讼的价值在于对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具有昭示作用,俗称的“电捕鱼”所破坏的不仅仅是渔业资源,而是整个生态环境。对于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犯罪既“打”(追究刑事责任)又“罚”(追究民事责任)能够有力地震慑非法捕捞行为,提高社会公众的环境资源保护意识与法治意识。
公益诉讼是“富矿”
诉讼法理论认为,利益受到了损害,受害者就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司法救济。但是,有些利益受损并不是单一的个人、法人利益受到损失。受害者是广泛且散布在一定区域的,客观上需要把分散的利益受损集中起来,以公益诉讼的方式加以维护。
我国普遍认为,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活动。
按照提起诉讼的主体不同,公益诉讼可以分为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作为国家公诉机关,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是其本身的职责所在。目前检察机关也在积极进行公益诉讼的实践,可喜可贺。
由于我国对公益诉讼理论研究的薄弱和公益诉讼实践的时间还很短,有许多理论的问题需要进行研究。例如,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区别,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小集团利益的区别,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区别,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与社会公益团体、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区别等问题,都亟待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探索。
可以说,公益诉讼在我国大有可为,但也一定会遇到各种阻力。对社会公益团体或者个人而言,这件事与你的利益相关与否以及如何证明这种相关性的存在,也许就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以两被告人非法捕捞为例,如果不是检察院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同时提起公益诉讼,而是社会公益团体或者个人提起公益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受理,也有许多操作性的问题需要解决。
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社会公共性权利,除了通过法律的普遍性实体赋予外,还要获得可诉性,这是法律救济的重要原则。2017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将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一修改,标志着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初步建立。但就实务操作而言,必定会遇到来自地方保护主义的阻力。在矿产资源评价中有富矿、贫矿之分,富矿指的是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的矿床或矿石,贫矿则反之。同样的道理,公益诉讼也是我国诉讼制度中值得深度挖掘的一块“富矿”。
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不仅具有建立的必要性,还有操作的紧迫性。只要敢于、善于挖掘,公益诉讼一定能够在我国结出丰硕的果实。特别是公权力遭遇公益诉讼时,人民法院应当如何作为更是众所期盼的重点之一。
假设某县检察院就县政府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不作为,向县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法院敢不敢依法受理、能不能依法裁判都有待在实践中检验。在上海,已经成立了跨区域的人民法院,这显然是为行政公益诉讼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具体的操作上更应当大胆突破,先行先试。
“摸着石头过河”
众所周知,为了维护生态平衡,保证环境资源的永续利用,依法规定禁渔期、禁渔区、禁用工具、禁止使用的捕捞手段是世界各国通用的做法。电捕鱼是国家法律禁止的捕捞方式。渔业法明确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根据相关追诉标准,在非禁渔区和非禁渔期,使用电鱼方式捕鱼,达到500千克以上或者价值5000元以上的,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两被告人采用加大渔网网眼尺寸的方式,使得捕获鱼类个体均较大。这种捕捞方式会导致各类受高压电流波及水生物死亡或个体受损。更为严重的是导致鱼类丧失繁殖功能,直接影响鱼类种群繁衍。显然,认定两被告人行为具有破坏生态的责任于法有据。
本案在依法追究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要求两被告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赔偿因非法捕捞水产品造成的国家渔业资源损失,并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经上海市崇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定,9次非法捕捞行为所得渔获物价值共计人民币75890元,而不是其他案件所指的“销赃所得”。
一审判决认定两被告人赔偿渔业资源损失75890元,所依据的也是渔获物价值。“渔获物”也许是一个公众比较陌生的术语,它是指捕捞行为所获得的物。相应地,“渔获物价值”也不是习惯上所说的批发价、零售价、市场价等,而是捕捞行为所获得物的价值。本案按照“渔获物价值”确定两被告人赔偿渔业资源损失的数额具有合理性。
生态系统是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群落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会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具有自调节功能的自然整体。
以渔业资源生态为例,长江是我国淡水渔业的摇篮,堪称鱼类基因的宝库,在我国淡水渔业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渔业资源总量大幅下降,一些经济鱼类资源已经走向枯竭。对水域生态的破坏手段多种多样,常见的有排放污染物质、非法捕捞、过度捕捞、外来物种入侵等。
生态是具有动态性、脆弱性、区域性、多因性的开放系统,某一种或者某一类物种存在的合理数量,是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重要条件。电捕鱼的危害性在于“扫荡式”的放电,导致过电水域局部“荒漠化”,增加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在电力所及的水域内,必然导致各类受波及水生物死亡或受损,侥幸逃脱电击的鱼类,其生理功能也会遭受不同程度损伤,运动能力、捕食能力、抗病能力和识别能力都会显著降低,并极易导致不育,直接影响鱼类种群繁衍。
生态修复的对象是生态系统,由于生态的复杂性,生态破坏程度认定、即时破坏损失价值、远期破坏损失价值、应急修复的成本、长期修复的成本等方面,都需要科学核定的技术与方法。
在当代,环境遭受损害后的首要任务是修复受损害的生态环境,这已经是人类的共识。2019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发布《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首次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责任方式。
《规定》明确,受损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判决被告承担修复责任。这无疑是责令被告承担修复责任的法律依据。生态修复是在生态学原理指导下,以生物修复为基础,结合物理修复、化学修复、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以及工程技术措施的综合方法。不仅修复方法具有复杂性,修复过程中人财物力的耗费也需要精准测算,这对审判工作而言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目前在我国,“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理念还处在确立的初期,“生态环境损害无法修复的,实施货币赔偿,用于替代修复”的原则还需要大力宣传。我们不仅要进一步细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损害赔偿范围、责任主体、索赔主体、损害赔偿解决途径,还需要明确修复责任的具体核算方法。
2020年4月26日,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也为进一步落实生态环境修复提供了有力的依据。